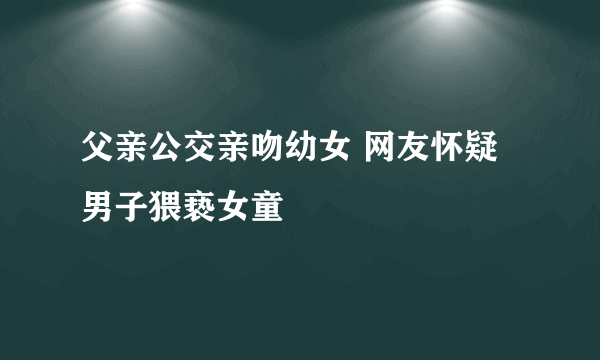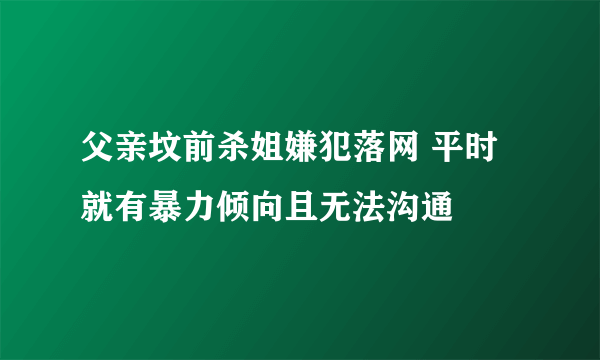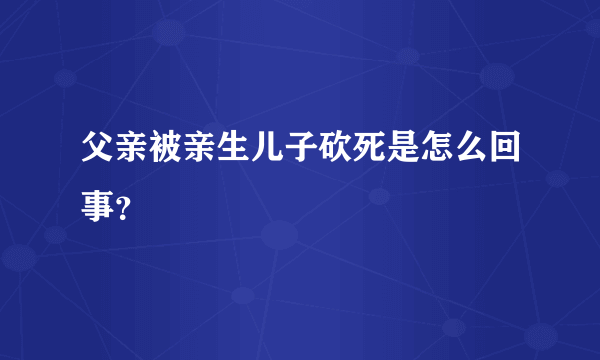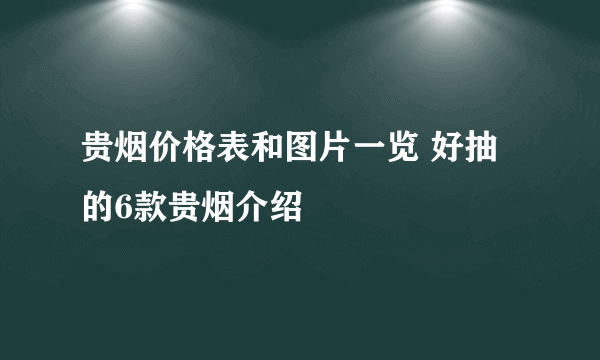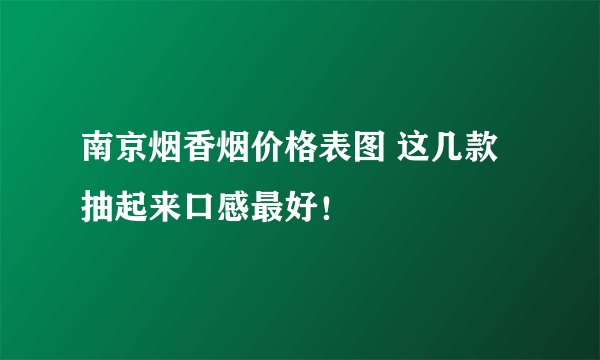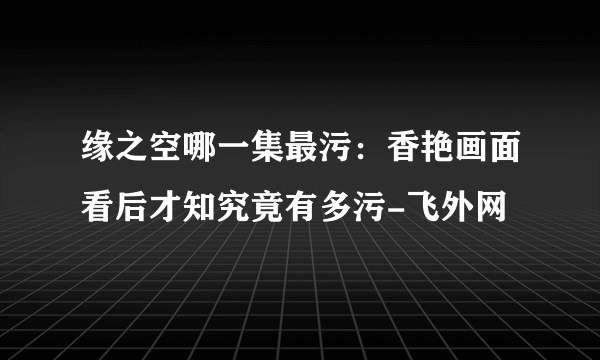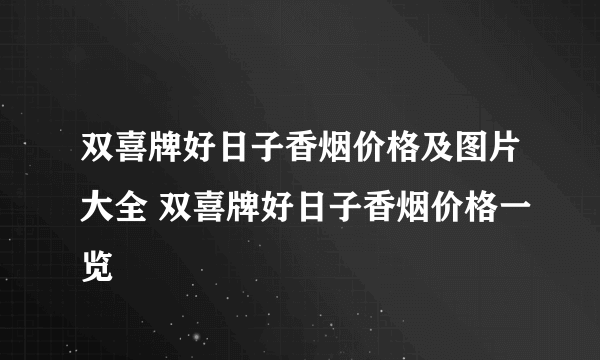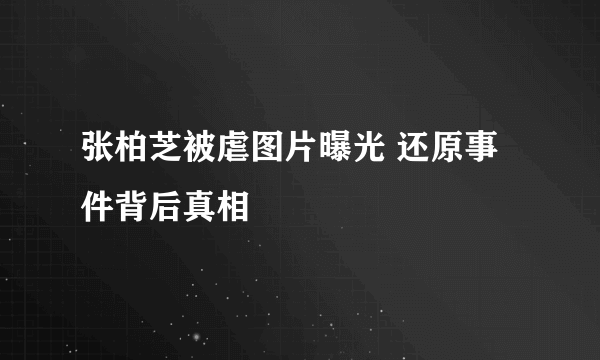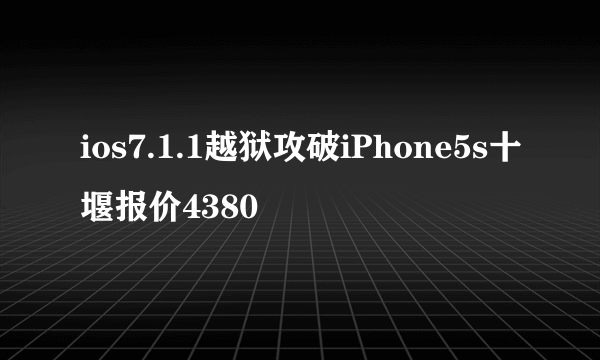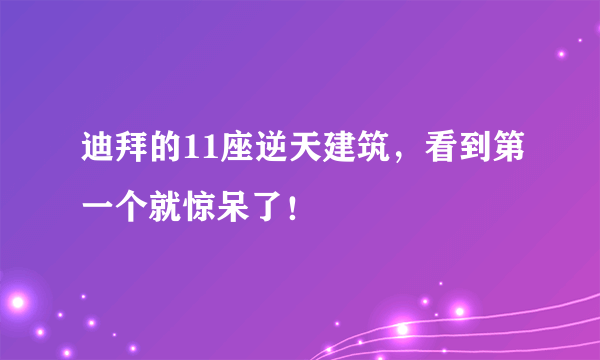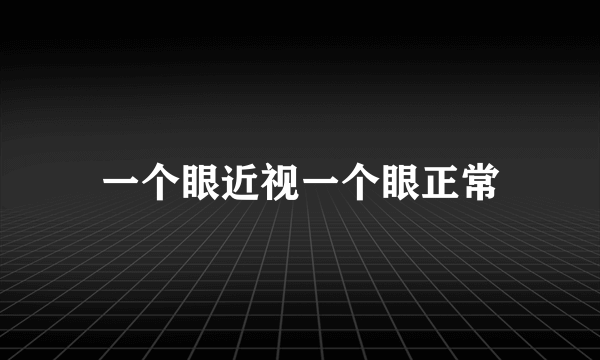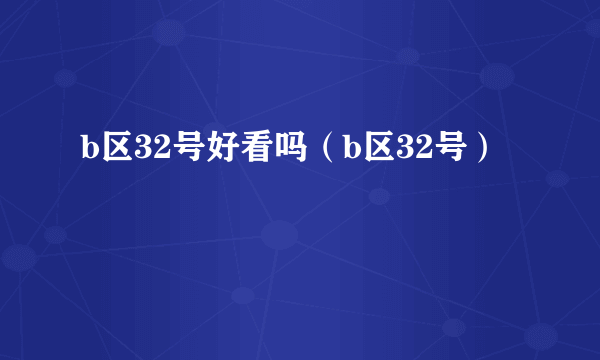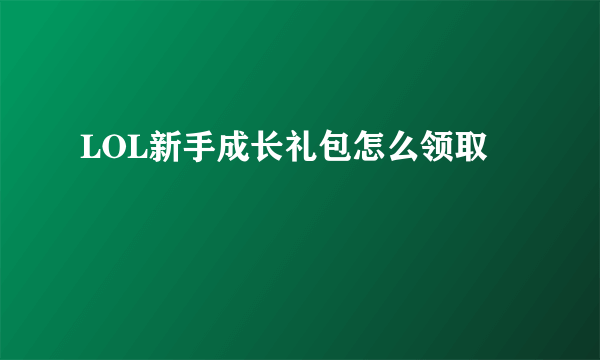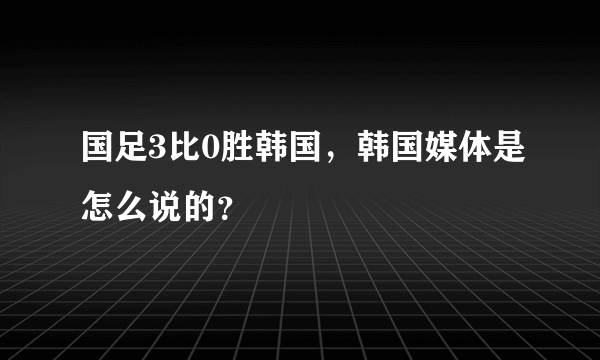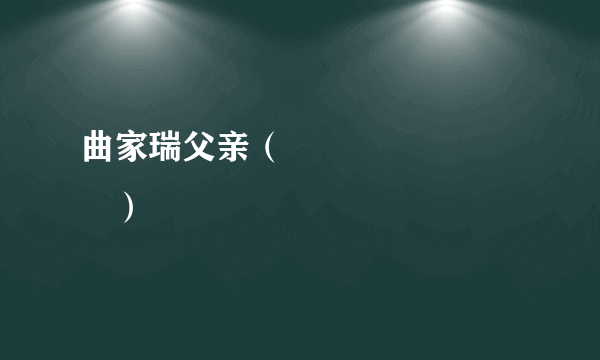
曲家瑞在深圳诚品生活《曲家瑞 你哪位》展览现场
“在任何领域,你要冲,一定会不知不觉被推上竞争的路,你要参加比赛,要拿奖。没办法,我们一生都在讨好别人”
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8期
文 |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梁翰文
图 | 本刊记者 大食
全文约 5390 ,细读大约需要 12 分钟
曲家瑞对细节挑剔且敏感:喝星巴克只能要五分之一shot,配上脱脂奶,比常温高一些,但不能太热。她曾有位犹太男友,每次点菜都会提出诸多要求,直到服务员翻白眼;轮到她看菜单的时候,马上讨好地说:“我都可以。”分手之后,她报复般继承了这个习惯。
进酒店,她得将工作人员房间一一看过,再择一入住。接受采访,更愿意背对着门而非时刻看到有人进出。个中标准极为主观:那一刻那个选择可以让自己心境比较自在。
曲家瑞收藏的公仔
她拥有丰富的经历,也具有讲故事的能力,这让她可以游走在不同主题的综艺节目中。在她的描述里,与跳蚤市场上渴望卖掉娃娃的女孩的交易变成了“我不想长大,她想长大,所以我们在那个台阶上交换了青春”。类似的经历常因她飞快的语速如浪翻涌,也为她带来了观众的目光。她的形象被节目构筑:言行如艺术般荒诞,情绪丰沛但脆弱,感情经历段段传奇却屡屡受挫,在传统中国家庭和美国教育的合力下完成自我塑造,与她紧密连接的标签是“做自己”。
节目停播的影响比她想象中要大:粉丝增速减缓,通告数量或主动或被动地变少。她的心态因之陷入低谷,画画不再顺利,终日惶惶,在经纪公司办公室对着老板崩溃大哭。老板放了她一段时间的假期,她飞去瑞典参加徒步,在屏幕上喊了“做自己”几年后,开始了“找自己”的旅行。这次“找自己”是50岁的曲家瑞对20岁的曲家瑞的呼喊。
大学时候,一位艺术家来学校观摩学生作品,曲家瑞作为三名学生代表之一给他看了自己的画作。对方看了说:“你是一个art smart的学生。”“那是多大的耻辱,等于对我说我做一切都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好的,是趋利性让我去做,而不是我真心想做。”她很难过,但是更难过的是意识到这可能一辈子改不了,“在任何领域,你要冲,一定会不知不觉被推上竞争的路,你要参加比赛,要拿奖。没办法,我们一生都在讨好别人。”
比起对人生观的冲击与改变,那次旅行她记住更多的是零碎的片刻:山峦的延绵与云河的浩荡,必须自己动手挖出的30厘米深大便坑和超过12公斤的行李。刚开始的两天晚上,她在帐篷里翻来覆去,想的是“做自己是一件自私的事情”,这么想的同时,她难得地拥有了跳脱讨好的瞬间。
旅行结束,她视野开阔,心情恢复,重拿画笔。但在自我方面,这次旅程并未给她带来实质改变,她依然在吃力地平衡“讨好别人”和“做自己”。
在很开心、很兴奋的时候,平衡会被打破。最近一次是从台北飞深圳时,明明在飞机上还兴奋地憧憬和讨论着马上开始的画展,下飞机后她突然想一个人待着,丢下工作人员跑上了一辆小车。司机问她去哪里,她说:“不管你,你赶快开,我受不了了。”
源头也是20岁的曲家瑞,那时她和好朋友们去玩,明明聊天很开心,她突然说去旁边拿点东西,就跑走了。在一棵树下坐了一个小时。朋友到处找也找不到,还以为她失踪了。
“人很奇怪,很开心的时候,就有另一个你跳出来说,不能这样,然后你控制不了,只能听他的,缓和,稳住。”
这些时刻——现实与过往的呼应、细节的放大、情绪的爆发……被曲家瑞称作“人生零点零几秒的瞬间”,这些瞬间让她迅速沉迷,又奋力抽离,继而反思人生。
以下为曲家瑞口述:
曲家瑞作品《interior(室内)》
撞墙算什么
1月初,我回到台北的工作室,里面的东西都搬到深圳了,难得那么空。我神清气爽,赶快画了一张自画像。经过前年的旅行、去年一年的展览,我好像安静了一些,我眼里看的、心里想的、手上画的,终于可以靠近一些。那幅自画像,就是最血淋淋、活生生、诚实的自己。我知道了,我还可以画画。
这次展览,有一面墙都是我各个时期的自画像。我跟观众交流,他们说画里能看到20岁曲老师的血气方刚、30岁曲老师的冲动与愤怒、40岁曲老师的沉稳与安静。我很开心,说明通过我的画,我们产生了联结。
1984年,我在申请库伯高等科学艺术联盟学院,终审要求用一个月时间画5个主题的画,前两个星期,我按要求画好了自画像、exterior(室外)和interior(室内)三个主题。学校录取率万分之一,我很担心申请不上,我的功课除了画画并不是特别好,那又是我唯一想去的学校,我一定要去。
画画的同时,我一直在跟学校打电话,希望能见一见其中一名主审委员。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一直拒绝我,说我们的教育人人平等,不能看到任何学生,避免动私心。可是我就记得我爸说,我们中国人见面三分情。这句话在美国也用得到吧。如果他们只看到我的学业成绩,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。我就猛打,说拜托啊,我绝对不会影响你们,我就来问几个问题,不是要你选我。接电话的行政阿姨被烦死了,终于在主审委员休息时间为我插了一个空,只有几分钟。
我就带着我的作品集、我得过的奖到了办公室,他看了以后说,还有什么要问我吗?我说,学校要求的五个主题我已经画好了室内、室外和自画像;高中校园里,我最喜欢美术教室,所以我要把这份荣誉献给它,室内画的是美术教室里面,室外画的是美术教室外面;自画像是我对着一张照片画自己。他说,你知道吗,我一年收到几万个申请,全部的人画室内都画房子里面,室外都画房子外面。我说,yes,你看我跟大家想的一样。他说,你错了,就是因为你跟大家想的一样,我们不会收你,大家都是这样画的,我们为什么要收你?我们要的是不一样的人。你其他画蛮好的,我现在往你资料里塞了一张黄色的纸条,意思是告诉看到这份资料的老师,这个学生我觉得还不错。但只有这样而已,你的主题画很糟糕。要怎么画,你自己去想。你要画出Kristy(我的英文名)的室内和Kristy的室外。你要想进这个学校,你能带给我们什么,而不是我们教你什么。
本来我只剩两幅画,两个星期绰绰有余,但全部重来时间不一定够。那我是不是就放弃前面几张,靠最后两张把分数拉回来呢?可是我也没完全明白他们到底要什么。走出学校,我站在一个十字路口,脑袋天旋地转,仿佛我的人生也卡在那个地方,不知道该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。
隔天我做了决定,跟老师请了十天假,要求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画画。我爸爸在纽约有买一个小房子,当时下起了大雪,外面一片白,我想到看过的那些卧薪尝胆、头悬梁锥刺股等等古代故事,觉得我这又算什么,好歹我有地方住,还吹不到雪。我就把自己关在里面,对着画纸和颜料想怎么画。室内非常难,我画到一直把纸撕掉,两三天进度为零。有天半夜我饿了,打开冰箱找吃的,看到里面的吐司、面包、奶油,我整个人好兴奋,想说这不就是室内吗?我用很抽象的方法乱拼一通,当时压力非常大,精神也很痛苦,色彩用得非常鲜艳,可能我想靠那个刺激自己。我非常耐心地一点一点上色,画好后说,yes,这就是我要的室内。这幅画就是后来我带上《康熙来了》的那张。
我又看看揉掉的那些纸,拿起来展开,褶皱的表面不就是exterior吗?我就用很写实的手法画了一张很皱的纸。当时我已经快疯了,就画了个分裂的我当作自画像,好像断层扫描,头在下面脚在上面。最后五张画完,我都寄过去,一个多月之后,拿到了offer。我人生第一次知道压力是多么棒的东西,能让我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这件事对我有很深远的影响。往后在学校,我们班有个菲律宾学生,每次作业都准时交,但都不会做到最好,永远是80分,永远安全牌。我不是,我一旦交作业,就会交到最不一样。不断自我突破,在压力下逼自己,撞墙算什么?再冲,再把自己往前推。
我现在教书,看到我的学生,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、选择放弃的时候,我很难过。想说,天啊,成功就在下一步,你就往前哪怕一步。可他们就是不懂,他们不要。他们会说,老师你对每个学生都这样讲。我真的不是。至少在那一分那一秒,我看到了你的不同,我看到你的可能性。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他可以成为什么,觉得怎么会轮到我?我知道可以,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
曲家瑞收藏的公仔
找自己怎么可能不自私
大概2017年吧,我不管做什么都遇到瓶颈,从我教书,到我的绘画创作,到我的演艺事业,到我对自己的评价,我都觉得已经到了谷底。
具体来讲,比如说粉丝,以前天天涨,怎么就慢慢不涨了,这些人跑去哪里了?或是说我本来很喜欢画画,可是不一定画得出来。或是我教书热忱到哪里去了?为什么我老想下课,上课就想下课、就想逃课,学生看到我,我永远在跑来跑去,一个礼拜三堂课,我只能专注在一堂。混乱都集在一起,一个事情推倒另外一个,再推倒另外一个。在家很烦,看到妈妈烦,看到什么都烦。感情方面也觉得是一团糟。我就想,我真的完蛋了,每一条路都没有了。
我有一个很棒的经纪公司,我都想要解约了,去找总经理谈,崩溃大哭,说让我走。他说不行,合约还有一年半。
其实我很不开心,觉得人生都不对,还想说,怎么我寻求很多帮助,都没有人理我?我就想,好,自己去找,也许离开家一趟,可是又不能离开太久,因为我妈年纪大了,我爸也过世了。刚好瑞典有一个国王小径的徒步,一听是国王以前走过的路感觉应该很棒,沿途有很美丽的风景还有城堡,我们可能会住在很贵的旅馆里面,每天刷卡。我当时是这样想。
没有想到到那边之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我带了两个大行李箱,他们说都不能带,因为太重了。我们住的还不是旅馆,是小木屋。一到小木屋的时候,我要煮水,就烫到了手,这真是一个不祥的预兆。团里全是二十几岁的男生女生,我最老。他们一个人可以背18到20公斤,12公斤已经是我的极限。我问了一圈,没有人愿意帮我拿行李。
晚上大家都睡了,我坐在门边哭到发抖,行李根本打包不了,我已经在崩溃边缘。我说,干!我转机三次飞到瑞典小镇上,都逃不了糟糕的生活,还让自己陷入一个更大的坑。
怎么办?还是要去啊。我整晚没有睡,6点多打好包。我很好强,第1天走得最快,殊不知那天之后我脚整个坏掉,第2天慢慢落后,才知道心里想赢是一回事,能不能做到又是另一回事。第2天下半天我就承认了,落到中后方,第3天已经在最后面。我发高烧,自己煮水,大便也要自己挖个30厘米深的坑。我开始意识到,不管你是谁,在这里都是适者生存。
沿途大家一起唱歌互相鼓励,一天要走12到14个小时,好几次都觉得要掉到山下。我每天都会反省自己:我人生做对了什么,做错了什么?在那里面看到的画面很远。第4天我做了一个梦,梦到我忘了一切痛苦,大自然接受了我。醒来我已经感受不到身体的痛了,走得越来越快。到了第6天之后我又走回了最前面,才知道要从最后一个走回来才是真的第一名。到终点反而没有觉得自己很伟大,超级平静。
我每天都反省自己怎么是一个这么自私的人。我想要来这个地方,为了找自己,把家人都抛在那边,本来照顾我妈是我的责任,现在就变成我姐姐、弟弟来照顾,这不自私吗?本来我觉得找自己非常好,因为我们需要找到自己才能开心,可是找自己的过程非常自私。
旅行回来我就快速创作,想做什么事情就做,我不能等了。以前总说,没关系、再说,就算到了50岁面临这个问题,我也觉得OK。可现在就不是了,我知道绝对不行了。
之前会抱怨娱乐圈延误了我,现在不会了。但是我知道画画时候的我和上节目的我存在冲突。去录节目觉得好棒,但下了节目失落极大,觉得刚刚那些太棒了,灯打得好亮,很有成就感,全部人给掌声,一下来之后会耳鸣,两三天都不能平复。接下来一两个礼拜,如果没有人发通告,整个人就崩下去了。或者我今天在节目上讲了什么,观众听了很喜欢,就有很多节目叫我上去讲。可是讲那个事情是我活这几十年来最精华的东西,给了之后就被掏空了一块,也许换来了钱,可是这块空了,要花更多时间去填满,其实很对不起自己,是出卖自己嘛。
我一开始就是一个傻瓜误闯丛林,后来渐渐就不去,现在不去了。现在我专注在画画上,这本来就是让我走向独立的能力。如果今天我什么都没有了,还有画画可以收留我。
我很分裂很冲突。以前我太不独立,住在爸妈的房子里,啃老族。大家都说我很自信,其实我非常自卑,我时时肯定又否定自己,想要每个事情都做得很好,可是又都做不好。又想哭又在笑,又痛又觉得爽,真是太可怕了。
但这不用调节,我知道停不了。我认识一个独立动画导演,十多年前她来台湾开讲座,我帮她翻译,在场的动画老师、教授问她,为什么你可以保持这么好的状态,还可以创造这么特别的作品?她就说,我虽然坐在这里,但我人不在这里,我跟你们这么靠近,但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防护罩在我周围,把你们全部阻隔开,我非常保护自己,不会让我不想要的东西入侵。当时我觉得很可笑,可是现在我好像慢慢理解了。
你现在问的是很细微的东西,每个人跟自己总有零点零几秒的瞬间。大部分时间我都跳过去了,不会停下来。可一旦那些瞬间抓住了我,我会停下来把它放大。在那个时间里,我会思考:每天浪费多少时间?浪费多少东西?我有没有真正对得起我自己?我到底在干什么?
问题的答案常会出现在我的自画像里,面对画画我绝对诚实。
中国人物类媒体的领导者
提供有格调、有智力的人物读本
记录我们的命运 · 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
往期精选
●终极一战:与死神抢人
●寻子十五年 “梅姨”拐卖案中的父亲申军良
●疫情时期百步亭:突然进入始料未及的生活
●温州 一座重疫之城的自救与挑战
●“重组”金银潭:疫情暴风眼的秘密
标签:曲家瑞,父亲